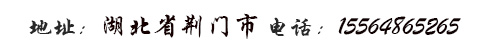记得当时年纪小系列书出版,看看宝藏
|
QQ营销求职招聘微信群 http://jyzhongg.com/xinwen/7142.html 儿童绘本作家蔡皋是中国原创绘本的拓荒者和泰斗,首位获得金苹果国际插画大奖的中国画家,波隆那国际插画展评委,她的作品还入选了日本教科书。她为孩子们画了《宝儿》,画了《桃花源的故事》,画了《孟姜女》《花木兰》,画了《火城》。她的作品又不仅仅是给孩子看的。她是艺术家,还是散文高手,是活泼泼的生活家,是人们心中的宝藏奶奶。她珍爱岁月时光中小小的快乐,路边的草,墙缝里的花,盘盘碗碗里的寻常吃食,在她笔下,都有了各自鲜活的灵魂。用她的话说,在童书里讲不够的,她就挪到面向成人的作品中去讲;在成人作品里展示不了的,复又归到儿童的图画书里去做——就像是南方女子做的“双面绣”,看似是一样东西,却常常能生长出两种意思来。 经折装绘本“记得当时年纪小”,一套六本的盈掌小书,在蔡皋的书橱里沉睡了二十多年的作品,终于在去年年底前面世。这是一套留住童年的书,也是一套不停留在童年的书。她从根源处寻找力量,给今日的心灵带来慰藉,而根扎得越深,人就能走得越远。 谨摘书中蔡皋回望往昔的人生自述以飨读者,这也是六本小书的“底色”所在。 “记得当时年纪小”系列 作者:蔡皋 乐府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底色 文 蔡皋 在做这套书时,我问自己,我为什么要做它,我还问自己,我的作品是什么? 我的作品是什么?它像是一泓清水,不大不小刚好照见我的天光和云影,照见我的生活。 我的生活和我的作品多与儿童、与民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它们有时以图画书的形式、有时以单幅画或其他形式出现,我都会看到它们在精神上的那种叠合。在童书里讲不够的东西挪到面向成人的作品中去讲,成人作品里展示不了的东西复又归到图画书里去做。如此看来,我的作品好似南方女子做的那种叫“双面绣”的针线活。 我喜欢针线活,喜欢绣女们制作绣品时单纯而专注的心思。在我看来,画家创作时的态度与绣女们一样,心中应有特定的对象,并怀有温暖的心思,那种作品是能打动人的。 作品终归是要面对他者,否则永远处于自话自说之境,这不符合创作者的本意。 我的家里有爸爸、翁妈、妹子们,外加一个重要人物——我的外婆。 我最喜欢我的外婆。 我外婆有一肚子故事,那些故事大都属于口头流传。传媒发生重要变化之后的当今,几乎再没有外婆讲这种口头流传的故事,新的外婆和外孙都在电视机前坐着,外婆的手里不用再做各种针线,因此也拉扯不出那么好听的民间故事。我们幸好有故事外婆,幸好外婆有做不完的针线活,我们亦有听不完的故事。我外婆的故事有腔有调,有栀子花、茉莉花的异香,所以我的生活变得有腔有调,且有栀子花、茉莉花的异香。 除了故事,我外婆还会有情有致地安排一家人的生活。她会做甜酒,会做坛子菜,放藠头大蒜的坛子里漂着芝麻,藠头又酸又甜,让人垂涎三尺。有一天,我和我的妹妹们没有节制地偷吃甜酒,大的几个没事,我的小妹则是醉卧床下,找她半天才找到。 我外婆似乎还是一个民俗专家。春节祭祖,办年饭,小孩子则玩罗汉,玩香棍子,香棍子用来做“毛姑姑”,占卜运气;清明则为外公扫墓兼踏青;夏至吃立夏坨(长沙人爱吃的一种用糯米做的小吃);秋至则做“秋至胡椒”;端午包粽子、做雄黄酒、看龙船。总之,有滋有味,四季分明。除了四季,我外婆还喜爱看戏。她看戏,我可以跟脚,因为我记戏文,还记角色,不仅记得角色,还要画这些角色,令她不敢小看。这样,地方戏自然不必说,过路的戏班子的戏也是有戏必看。我喜欢老戏台,喜欢那种戏院气氛,直至日后或多或少把它们搬到画里去才觉熨帖,就是自此开始。 我外婆会做针线,最“辉煌”的成果是做鞋子。搓麻线,打衬壳子,剪鞋样,纳鞋底,用楦头给鞋定型,一条龙。别人做鞋是一双双做,她做的鞋是一箱箱。她去北京姨妈家定居之前,为我们姐妹做了可供三年穿的布鞋,我们姐妹在此时已有五位,一三得三,二三得六,她老人家不就做了一箱?于是乎,我外婆提拔我做帮手,我负责给一双双鞋做记号,在白鞋底标上咪一、咪二、咪三,玲一、玲二、玲三…… 敬神的功课有时也让我做,我爬三级梯子往神龛上插三炷香,以棍击磬,听它发出三通脆响后,双手合十。然后是天井,天井南向的墙上有三个插座,皆铁制,那儿没有牌位,祭的是天。我在不知道天的情况下,感到了天的神圣。这种庄严的事情做着,人也就懂得有敬畏,人生在我的眼目中渐渐显出庄严气象。 我外婆是个魔法师,她有层出不穷的单方,那些单方出奇有效,幼年的我亲眼看她救了我四妹和一个叫坚弟的男孩的命。我还亲自服过她的单方,不出半个钟头,它止住了我剧烈的肚子痛。她教她的亲戚朋友在秋至时分,按时按点制作胡椒,那种胡椒她冠名为“秋至胡椒”,畏寒怕冷,肚子痛,吃一把很管用,有时还会从她的抽屉里找出小包茶似的粉末和香灰,那也是灵物,放在开水里一泡,灌给我的妹子喝,居然有用。现在依然觉得不可思议。 我的外婆送我最好的东西莫过于自信,当我能领着我的二妹摇摇摆摆穿越小巷去上学,外婆即教我们“出门看天色,进门看脸色”一类。“进门看脸色”比较容易,省得挨骂,“出门看天色”我看出的是“天天是好天”,就是不肯带伞。背着书包、拎着石板、牵着妹妹,还要夹两把伞,而且是纸伞,是何等景象?所以雨一来,我就赤着脚或是不赤着脚跑回来。不管我赤着脚还是不赤着脚跑回来,我外婆总是预备有表扬给我,赤着脚是因为我识得艰难,爱惜布鞋;不赤着脚是爱惜身体,免得病,省得钱,一样是懂事。这种启蒙使我拾得一份自信、自立的观念,并且学会了最为原始的辩证法。这不能说我外婆不懂得辩证、不懂得教育。 我开始画画,且有种大胆的作风,则要归功于我全家的宽容。我爸一年四季在外头做事,自然对我们是大宽容。外婆和我翁妈,加上放假归家的姨妈——一位表演天才,都是戏迷。她们不仅让我看戏,参与她们外交,而且送我颜色,加起来就是大宽松。在没有颜色之前,我会从床脚下耐烦地摸找松软的木炭,在一张张门背后的粉墙上画大型壁画,乱七八糟,墨墨黑黑,她们也不骂我。我的芳邻齐嫂子,则或背或抱着她的小宝宝站在我背后紧看,意犹未尽之时居然请我去她家的门背后也画它一幅,让我这个“画家”着实兴奋了一把。我有几个读者?包括那个小宝宝,我妹子,有一桌人咧! 童年的天空,飘着风筝;童年的衣服,花花绿绿;童年的气息,混合栀子花和茉莉花的异香;童年的色彩,传说一样奇妙。我找童年,同时找到了民间。原来,我本民间,朴素深厚的、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民间。 在我懂得去一所好的学校可以继续读到好书的年月,我被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录取。湖南一师学校是个师资力量强、藏书很丰富的学校,我欢喜不尽地在那儿读了一些好书。当对《海瑞罢官》的批判拉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序幕之后,图书馆大量图书被禁,我只能读到郭沫若、鲁迅和毛主席著作。在批判《燕山夜话》的浪潮中仔细读被批判的那些原文。幸好此前已读过不少中外名著,包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作家作品,大都囫囵读过了。 无书可读的岁月,我还是可以借到手抄本的书稿,借到好抄本,譬如古文笔法一类的书,我就抄书,抄书比借书还管用,我借此能背诵一些好散文,而笔记本至今还保留有一本。为此,我没少挨批评。我有机会还会画点画。画画多指为墙报或油印刊物画插图,偶尔停课去画学习毛著的标兵,我把这类事都当创作做。 罗校长罗三德也是很有味的人,他喜欢下班级亲授诗词课,专讲毛主席诗词,讲得高兴时声情并茂,人会一上一下,坐在后排的学生就会看到他忽地没了,忽地又拱出来。有次支援“双抢”,罗校长也去了,他有胃病,每天只能吃二两米稀饭。他忽然在我旁边插秧,一边插秧一边问我:“蔡皋,你看这个插田容易些还是写文章容易些?”这话问得不好回答,我一时无语。但却知道他是看过我的作文的人,很是感激。不料他这句话后来被人篡改,成了他在“文革”时期“争夺接班人”的罪状。 我的美术课王正德老师、语文课曾令衡老师皆是很会上课、很有本事的人,这样的老师第一师范还有不少。我听他们的课总有神采飞扬之感。 我欢喜我的母校,虽然所有的欢喜皆有不欢喜卧底,但我把它们加起来喜欢,我喜欢我敬爱的老师和可爱的同学们。在那段慷慨激昂的岁月,我们班级称得上波澜不惊,我在这种对比关系中完成人生初步的预备功课,这种功课使我在走向社会时已懂得了什么是我根本的需要。 毕业之后,在当地(株洲县)文化馆敬绘了一年的毛主席像,然后“安安稳稳”地去了该县最为偏僻的山区太湖小学当一名教师。 去太湖,起初是作为一种惩罚。不料,我因此却获得六年亲近乡土的机会。 太湖并没有湖,“太”字是方言“大”的谐音。之所以叫作太湖,是因为当地山与山之间的谷地如绿浪滚滚,其状若湖。 我喜欢山村,我所在的学校由古祠改建,祠里的六朝松依然顶一团绿荫,上下课的钟声敲响,远近山谷都有回声,这可爱的田亩、山谷因钟声而平添了一种禅意。 山村的一草一木,一山一水,在我全是一个好。上课堂堂进,下课当农民,无论如何辛苦,这个已知春插秋收、砍柴担水“无非妙道”的人已存有一种念想——在生活的艰苦中体味人生深层的喜乐的念想。我的思想境界渐趋明朗,我的生活也日日是好日地好起来。 (文图摘选自“记得当时年纪小”系列,文字有删节,标题为编者所加。) 找记者、求报道、求帮助,各大应用市场下载“齐鲁壹点”APP或搜索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xionghuanga.com/xhcd/10949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记忆中的青蛇第一个经典,第二个妖娆,第三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